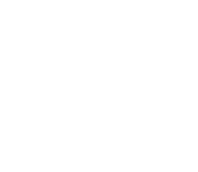编者按:新时代中国美术高峰的铸就需要新的美术理论。立足于中国国情、展现中国特点、建构中国美术话语体系,已经去世的梅墨生先生生前对中国美术发展颇有洞见,本刊分两期刊发他的《中国画的人文标准和美学追求》,以飨读者。

探讨中国画标准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脉络
目前,艺术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莫衷一是、错综复杂,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画得很差也可以通过包装、推荐和宣传来混人耳目。今天我们主要探讨中国画的标准问题,也就是怎样的画才是好的中国画。要知道,任何高深玄虚的理论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画面上。
首先要明确的是,传统中国画的立足点是站在中国画的文化脉络里。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画要现代化和国际化,就像我们现代人要享受现代文明给物质生活带来的便利。我们承认艺术家并不是活在真空里,艺术也不能束之高阁,现代人生活的空间、文化背景等都与中国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所用的笔、墨、纸这三种工具都与我们的中国画有关系,因为这是现代人生产的工具材料,在这个时间、空间里,我们谁也逃脱不掉现代的影响。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代人用的宣纸就很难画出徐渭那样的画。但是,对于中国画的国际化问题,我们不禁要问:“究竟国际化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我认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国际化标准”。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后现代”这一标准无疑是最时尚的,但这与传统中国画关系不大。因此,探讨中国画的标准问题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
中国画人文精神主张以和为贵以和谐为美
中国画有何种独特的人文标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国家。我们现在进入工业化和科技化的历史不超过100年,是被西方的洋枪利炮打败后被迫开始的。1840年以后的中国洋务派才开始认识到要学习西方器物和科技的长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的文化确实悠久,糟粕与精华并存,当然以精华为主。所以,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人,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这二者是相互作用的。
传统中国画追求的是从容的状态与平和的心态,展示的美是一种和谐之美。传统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追求从容的生命状态。古人画山水要“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还要在书斋里慢悠悠地喝上一杯茶,然后三五个茶友、画友在静谧状态里才能创作中国画。但这种创作方式在20世纪出现了问题,因为画家的生存背景和生活节奏变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思潮都进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现代画家并不赞同传统中国画要求的那样画得平和,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传统中国画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相合、人与天相合,是天人合一、人人相合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也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不会有中华文明五千年以上的绵延与传承,追求和谐是中国古典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无论院体派还是在野派,无论廊庙还是世俗,无论民间画工还是宫廷画师,他们的作品中都要体现出这样一种和谐之美。
和谐之美在中国传统绘画里的典型体现,就是从来不画十字交叉的图形。中国传统画家作画的时候一般都不做十字形的正交叉,因为这为中国文化所忌讳。画面中也不会出现三角形或者三个交叉的线在一起,因为传统画家认为三叉纠结、矛盾,让人心理上不舒服,容易联想到很锐利的感觉。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里,十字是耶稣受难的象征,十字架代表为人类殉道的精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善的代表。西方文化绝对不忌讳十字交叉,后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用符号表达艺术的时候经常会采用十字符号,但作为一个受到中国文化浸染而爱好艺术的人只要看到十字交叉符号就会自然地产生排斥。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圆形会愉快,心理上表示可以接受,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在追求阴阳平衡的文化里受过熏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但实际上与绘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相联系。
人类的文化认识有相通的地方,所有的人类都有一个时空概念——过去、现在、未来,基督文化和天主教文化里有“圣三位一体”;我们中国人讲“天、地、人”三才合一;佛教里讲西方三圣——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中国民俗信仰中有福、禄、寿“三星”。世人对“三”都有共识。数字是有深层含义的,不同的宗教文化有不同的偏好。比如基督教文化讨厌“十三”,《圣经》故事中《最后的晚餐》表现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了耶稣,十三是不好的数字,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从不忌讳十三。中国文化喜欢“十三”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讲阴阳,阴阳下面是“三才”,“三才”下面是“五行”,所以阴阳、三才、五行,然后是八卦,八加五是十三,因此中国人认为十三是非常好的数字,这是中国人的时空观,这是东方的智慧。
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悠久的传统,具有最深层的文化底蕴,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主张“打倒孔家店”,开始把老祖宗的东西都扔掉,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对封建文化、破除封建迷信等,现在的人们对这些越来越陌生。因此,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心理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中国画也是这种情况。现在有很多画根本不算是“中国画”,却要拿到中国画里来参与评判,在材料工具上没有关系,在美学理念、文化标准上没有关系,在语言表达、技术层次、方式方法也没有关系,对于何为中国画这一概念也不清楚。中国画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用圆锥形的毛笔画出刚柔变化、丰富无比的线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笔墨韵味,并表现一种事物的形神兼备之美,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无法评判中国画。如果不用传统中国画的方式来表达,并且表达的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旨趣,它就不是“中国画”。
总之,中国画的人文精神是主张以和为贵,以和谐为美。儒家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人在艺术领域的表达和追求不只是为了画一张画,其所有的艺术行为在本质上都要指向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有益身心、修身养性。在这个基础之外可能会有其他的附带利益,比如说知名度、获得功名利禄。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人并不具备艺术家的品质,也没有艺术家的心,也不是用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世界,更没有带着一种对艺术虔诚敬畏的心来从事艺术,这样的状态想画出一张传世杰作是不可能的。西方学院式教育就导致这一问题,不管学生的禀赋如何,大家统一开始学习。我们中国人却不是这样,虽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优秀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因材施教。古人讲“自知为智,知人为明”,现代人往往没有这方面的明智。那些真正能够把心静下来的人就会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理念,能够真正执着做自己事情的人终有一天会有所成。
中国画以虚无为本以虚实相生为美
中国艺术尚虚无、尚虚境,主张以有限包孕无限,以虚无为主。古人所说的“道”其实就是中国人做人的道德之本,在绘画里就是画面要表达的道理和美感。欣赏艺术后,观者的感受是伤感还是兴奋?是愉快还是沉痛?是消沉还是愉悦?不同的艺术有着不同的功能,艺术以虚无的东西主宰着人的存在。很多前辈画家常常说这个画“高”,这个画画得“虚淡”,因为虚淡合乎道的境界。这张画给人感觉很“松动”,因为“松”接近人散开怀抱的状态。人近乎与天地万物自然而然生长的状态,这就是美。董其昌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我手,眼前无非生机。”
如果画家有一种天地意识和超越现实的胸怀,那么他看待事物的心境就不会小,其气场自然就会很大。气场大画出来的画就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大气磅礴的画了不起。比如徐渭,他一生命途多舛,但他的胸襟和气场很大,他的“气”越是得不到施展就越会往外喷发到诗画和戏剧上面,所以成就了徐渭的奇文奇画。虽然在现实中,他的肉体并不幸福,但他的心灵还有释放的机会,可以偶尔狂放自负一下,可以在困苦中求得自己内心的满足,以此来安顿自己的心。徐渭的代表作《野葡萄图》上面的那首题诗很著名:“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胸襟气度,才成就了徐渭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奇迹。
 图为《黄甲图》,明代徐渭作,故宫博物院藏。
图为《黄甲图》,明代徐渭作,故宫博物院藏。因此,作画要以虚无为本,以虚实相生为美。以虚无为本是中国哲学的独特追求,西方哲学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西方天体物理学认为宇宙源于大爆炸,爆炸之后就是一团能量释放,按照他们的说法,宇宙现在仍然还在爆炸中。但中国的道家学说认为,万物都因宇宙的浑元之气变化而成,中国人所有的理念都来自“元气论”。正如唐代张彦远所说,“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中”,同时说“夫物象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但是,近百年的美术教育都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叫“造型”,以造型的观点来画中国画永远也画不到多高的境地,这是因为西方的艺术以科学为基础,从科学出发,逻辑学、光学、材料学、化学、透视学,这一切以科学为基础。中国的文化艺术根子是哲学。中国人认为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是元气的运行,所以南朝谢赫在“六法论”里的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现在许多中国画根本没有气韵,更算不上生动,而是杂乱气、阴霾气、支离破碎气,这些不正之气在当今的一些中国画里全有,但就是看不到阳刚气、和气、大气,越来越没有正气。
在中国美学即为道德美学即为伦理
中国的人文精神主张人有多高画就多高,生命的经历、文化的积累与艺术的成熟是同步的。急功近利成就不了好的画家,梵高、拉斐尔、莫迪里阿尼他们都太早熟,艺术生命不过20年。可是中国画家在三十七八岁时可能还刚入门,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例如吴昌硕38岁还没有开始学习画画,后来才领悟到以书法金石的笔意来画画的诀窍。世界上有知识的人不少,但是有智慧的人有限。有知识的人会耍聪明,结果反被聪明所误,而有智慧的人则从来不依仗自己的聪明。所以,中国的文化主张要修养心性、要沉淀、要积累。潘天寿先生给人卓然而立、挺拔不凡的感觉,他的画论里讲:“至大、至中、至刚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为艺必登其极,为事必得其全。”这就是他的人生智慧和信念,如此才会出手不凡。中国的艺术是晚成的,讲究大器晚成、厚积薄发,如果是真心地热爱艺术,一定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你用多少工夫自然而然就会回报你多少。具体到中国画中,不同的画家有着不同的笔性,不同的画家画出来的是不同的笔线,笔线来自人的笔性,笔性是由心性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性才会有什么样的笔性,画画不只是简单玩弄笔墨,明心见性、修身养性是很重要的,终究是画家的心理世界在主宰笔墨和驱遣画笔。前辈画家们教人画画时往往会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这是因为在中国,美学即为道德,美学即为伦理,中、正、厚这三点既是艺术美的要求,同时又是伦理道德的要求。
中国画是艺术不是科学艺术不同于科学
中国的文化讲“元气论”,讲“阴阳”,讲“一气之流行”。中国人用心气和元气来画画。中国哲学认为“元气”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本质,而中国画要表达的是生命的生机,以气韵生动为美。“气韵生动”这四个字其实就是生命的活力、韵律和生生不已的状态。中国的文化注重“中”,不走极端,西方的文化不忌讳极端,例如超写实主义、极简主义、抽象主义,甚至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等都可以得到发展,西方的艺术其实就是“极端主义”的表现,而中国的艺术是中庸的表现,无过无不及。当然中庸也有中庸的弊端,比如说中国人不愿意冒险,西方人走极端可以探险、冒险,西方人有中国所没有的猎奇探索精神。中国是阴阳文化,踩高跷走平衡,不走极端,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观画,重在看其整体的立意、画面形式感和美感,以及整体的精神气象。所以,讲究中庸之道,主张以虚无为本,虚实相生乃是中国画的独特美。画面偏实一点就是唐画、宋画,偏虚一点就是元画、明画,偏实一点就是工笔,偏虚一点就是写意,虚得更大就是大写意。所以,中国画主张以哲学为用,以哲学作为指导思想。由于西方注重逻辑,以造型为本,无论是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超写实主义、抽象主义都是以造型为出发点。中国人画画是以养气为出发点,这个难度更高。按照西方的观念来看,黄宾虹的画确实不符合造型规律,但“近看不似物象,而远观则景色粲然”。西方人画画从物出发,最后的变形也是以造型为基础,例如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画中的变形。中国人画画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画有形神皆似和形不似而神似这两个脉络,追求超越的哲学境界。中国的写意画不会是纤毫毕现,必须敢于省略,否则永远画不了写意画。但西方人必须依靠造型作为基本的依据,这是中西方绘画很大的区别。
看历代名家的作品可以体会其中“线”的意味和底气,体会其薄厚、尖钝、拙巧、粗细、刚柔、曲直等,个中的趣味非常丰富。另外,中国书画必须玩味原作,原作的价值是复制品所不能比的。中国画要在有限的笔墨点画形象之间去感受存在的无限性,领会宇宙时空循环往复的阴阳转换之道。好的中国画要抱气,不能散气,但现在对中国文化有很深体悟的人越来越少。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画是艺术,不是科学,艺术不同于科学。艺术的真实不是客观的真实,艺术的美来源于生活与自然,但是与自然不完全是一回事。
中国文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人以圆融为美,最后表达出来的是圆的意蕴,古代的人物、山水、花鸟这些经典的作品莫不如此,这就像是太极图中间的S线,也许它只截取一点、一段、一角,但只要它包含着曲和圆的势,虚线延展后就能抱成一个圆。我们一个小小的画面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囊括进去,要运用以一代十,以一代千、百、万,以小代大、由近及远这些手法进行比拟和幻化。也可以说,中国画就是在极少中看出多,在极小中体会到大。所有向外延展的笔画之间都包含着圆曲之势,正如黄宾虹先生的太极图示范稿。宋人有很多团扇作品,感觉隽永、高古,具有某种永恒的欣赏价值。必须合乎“道”才成为经典。中国人认为的“道”是一阴一阳,阴阳并用,阴阳平衡,合乎阴阳转换的道,是相对立相统一、相辅又相成的关系。中国人所体悟的人道、天道、事物之道都是要遵从于“天”的道理,所谓“天”的道理就是自然造化的法则。西方人没有发现阴阳,但西方人有近似的认识,比如爱因斯坦就曾说:“我们的文化是以逻辑学和实验主义这两个东西组成的科学。”中国没有这样的思想体系,但中国人竟然不用这样的科学也能达到类似的认识程度。我们的阴阳、五行、八卦这些理论不但不封建不迷信,相反,我们还认为它们是先进的。中国先民的智慧并不落后,现代科学在不断证明中国古人的道理——东方智慧。
西方人的近代文明主张科学至上,唯物主义,科学万能。西方学者马尔库塞对此早有批评,这实际上是人的脑袋全部被工具化和物质化的过程,他称为“工具理性”。我们中国人希望一幅画里要以圆为主、方圆并用,就像阴阳并用一样,如此才成为一个完整的道。有阴阳才有世界,所以阴阳互相依存,既对立又统一,互相作用。因此,我们在画画的时候直中要有曲,方中要有圆。冯友兰认为,人生四个境界中最后一个境界就是“天地境界”,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是圆融、圆满、圆浑。这是我们先民体会到世界存在的道理和运行的规律,同样也是表达和揭示“道”的美感所必须依存的原则,但要揭示这个依存原则很复杂,必须通过形象来表达。所以,“气韵生动”的总原则也不能摆脱这一点。古人强调阴阳、虚实、刚柔、曲直、疏密、开合、聚散、动静互相作用,一张好画,笔墨本身的美必须具备干湿、浓淡两个层次。干湿、浓淡这四个字在中国《易经》的思想里就叫“四象”,具备了这“四象”的墨法,在视觉上自然就很丰富、充实、圆满。
生命本体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核心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核心是生命本体,李泽厚称其为实践美学,西方美学家柏格森主张生命本性,其实中国文化是最典型的生命美学。中国人论艺术和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生命的状态,用人生和天地万物来做比拟,用飞禽走兽来比拟,书法里所讲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惊蛇出草”“飞鸟出林”以及筋、骨、血、肉、气这些都是一种生命状态。所以,中国的美学不论书法、绘画、戏剧、诗词、音乐,乃至养生和武术无不以生命的动静、本质的美为真美。宋代道(理)学家是揭示宇宙存在道理的高人,例如道学家程颐解释什么是“道”的时候就说,“窗外阶前春草绿”就是“道”,台阶上春草萌生,茵茵然、萌萌然往上生长的这种状态就是“道”,这个解释很形象通俗。我们在这个时代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体悟,如何看待所谓的道统、元气、阴阳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真实、朴素是中国农业文明最基础的因素,实际上,道理、元气这些东西在艺术里就变成生命中的自我修为,所以,生命美学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种艺术品格,艺术有什么样的品格是由创作者来赋予的。
古代讲画品常用的是神、妙、能、逸四格。“神、妙、能、逸”这四个字用得最多,“逸”就是超逸,就是离开现实的红尘和名缰利锁的生活,因此有奇逸、高逸、超逸等说法。黄休复把“逸品”列为第一位,王国维也说“诗人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他认为“入乎其内”才能得到它的妙意,“出乎其外”才能够超然物外达到高的境界。生命美学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要安静从容、淡泊名利。齐白石的画不是高逸和超逸,而是入世的真实情感,雅俗共赏,但我们绝不能因为齐白石的画通俗就低看他,他作为一个平民能有这样的洁身自好和高贵气质是很难得的,齐白石的清高在于洁身自好,平民出身且喜欢日常生活,很真实。
画面给人的感觉和透露出来的“气”就是生命美学,以生命的常态来感受这件作品,那么这件作品映现的就是那个人,可能会有不完全对等的时候,但只要他是真实表露就是对的,越在下意识时候的表达越是真实的。中国的写意画是无意于佳乃佳,必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自己,一旦进入自己要表达的时候就变成本性的流露。“画如其人,人如其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画是生命的美学,一切都是生命的动静。另外,并不仅仅只有动态是生活的,中国的文化主张“万物静观”,在静中观察天地万物,澄怀味象,人必须放下所有才能澄怀味象。只有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够体悟天地运行之道,才知人终有一死,这才叫悟道,才知道所有现实的所得不一定永恒。“澄怀味象”中的“味象”就是体味和玩味天地,西方人说的形象、造型是“小象”,而中国人所说的味象不是形象而是“大象”,实际上是“天道”和“天象”。因此,小中能见大是中国画的特色。“小中见大”就是以个体的生命合道,达到澄澈的状态,静观万物,从容不迫。
(作者为当代书画家、评论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5年第14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