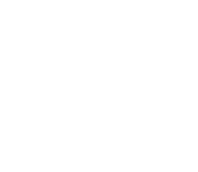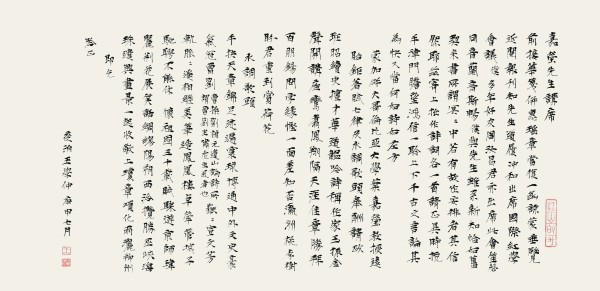
鉴于目前中国书坛注目于传统技法之研究,而忽于无迹空象之开发,所以作一次发言,重点谈书法是一种融会哲理的艺术。其他艺术虽然也透露出人生、美感、情思等多种观念,而体现在书法之中的却更为集中,充满了辩证的关系。谈“有”的艺术很多,我主要是谈“无”。
书法的哲理在哪里,是否凭空而造?不是的,书法透露出对人生的认识、观念、哲理。为什么在中国而不在其他国家产生书法,其中就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道,即最高哲学原则。每一家的哲学都指导着书法的体现,但中国在魏晋六朝时,佛道并提,解释世界的方法基本相近,包括儒家观念在内,基本上追求质朴,内涵如许慎解释书者如也,蔡邕解释为书者散也,还有解释为字为心画,白纸写清念,绘事而后素,与西洋人重物质、东方人重意念十分有关(即精神)。西洋油画方法与中国水墨方法即可证明。而使中西艺术分途,道家以无为景,佛家以禅学得体,书法上出现了经学派(这是我的分派解释)。他们艺术心体可以最完美的体现在书法上,成为书道合一。古人说其言近道,即是其中有哲理。
那么书法怎么证明是体现其哲学意念的?在我看来,中国书法类别虽多,但均从其哲理意义上体现。在此理论基础上,即可看出有政治家书如李斯;太宗、高宗(赵构)、康、乾或可称为帝王书;郭沫若文人而知政治书,是他的哲学观而定,一派正统书气象;军事家书,像岳武穆的字“还我山河”,大部分虽非岳飞亲笔,但字形总有所据,其字恢宏奇伟,气壮山河,有将帅之气。即拿毛主席书法,如果与倪云林相比,一个显示逸气,如文人画家书,而一个则明显是政治军事家书。如李白“上阳台”,杜牧“张好好”,则是诗人书。欧、柳、颜、赵虽然是封建臣子,但因其从政少而写字多,且功深笔正,是可以为书家字,其字可以为后世学字人的规范模楷。书家也自视为正宗,而非他人为旁门,比如赵孟頫即是以复兴晋唐为己任。最后还有释道书为数也很多。道家以吕洞宾为代表。董其昌评论吕字,说他近米,并说神仙还在学人间的字。佛徒书字更多于道家,如智永、怀仁、怀素、张闲这是有名的,一般的更多了。释子的字具有祥气,常写经文偈语,如写经生那就为数更多了,我一直立论,书法除碑、帖二系外,尚有经系,包括写经以外的摩崖刻石,立此一说以补阮元之不足。当然还有胥吏字、冬烘字、馆阁字。从以上所举即可看出,一个人的哲学信念,常常指导着他的书法,所谓书如其人。首先是他的哲学信念是什么,如李白浪漫好神仙,其书风飘逸似有仙气;颜真卿忠贞之臣,书有刚正之气;赵孟頫评为“天水之裔”,书有媚骨,可能也有他的哲学观念在,赵孟頫写了许多心情十分矛盾的诗,表示其忏悔心情。
书法论字之法,多重结体用笔,前人已阐发无遗。我在这里主要谈的不是这些,而是谈一下中国字的无形迹处,就像佛典所谈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我所探讨的,即是前人较少探讨的无迹与无象。
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书法是一种单线条的艺术,没有颜色,没有浓淡,但是从一字的布局和整幅的篇法来看,无迹与无象均是书法的重要因素。一般人认为字是笔画安排问题,而实际应是空间留白问题。如果一点如高峰坠石,没有石的空间坠下之势则点的力量何在!一篇行草,大小参差宜于相间、相生、相破,我认为是虚的占领。布阵易得其多,难得其少;易得其平,难得其势;易得其伏,难得其起。得其多者字无虚实,累牍连篇,少空灵之气;得其平,字如算子,不得其鳞羽参差之势;得起伏字,如贴片涂鸦失其立体,何况大小相犯,不得相生,锋芒相触,气流难贯。李北海为得势之始,马夏为空系之始,孙过庭说得意不如得势,字内得势,字外更要得势。
自从邓石如提出计白当黑论,书法与篆刻的空间观有一大进展。在纸上写字,黑者为有,白者为无,知白而守黑,黑者为有象,白者为无象。书家使无象而生有象,但既生有象,便有实境,实境又生空境,实境易得,空境难求,然而二者依,空境要有情态,空象难求,无迹易忽,重于点画,忽于行间,书如兵阵。古人论述甚多,用兵以少胜多,布局也当如是。孙过庭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为终篇之准。王義之的老师卫夫人有笔阵图,提出横如千里阵云,笔如兵,纸如阵,执笔如帅。大体说来,作字前布字有预想,但预想究竟有限道变无穷,克敌制胜,随机应变,所谓消息多方,又在人的智力之强弱。特别是行草书,要随时判断布局与布势,或强或弱,或失或救,或开或阖,如良将之率兵,游鱼之戏水,白作黑论,白中有书眼。中国画至南宋马夏一出,极大的改革与创造在于无迹与空象,传到日本成为南画,到八大山人,到达极高之空境。书法领域尚少开拓,大概书人保守,但空境不能体会为无象,书中如悬针垂露,都以空象而决取其长短,使意味盎然而无尽。元气周流才能得到,气如不流,意自迫塞。如苏东坡《寒食帖》,有清气扑人之感,可以想象到他在黄州失意宦途,蹭蹬官场,寒食的况味,由其空象无迹引发尽致。楷书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古代称他写的如见少女流荡于波间,皆足以为明证。无迹开拓从李北海、黄山谷,到善于大小伸缩的板桥、许友。
当然书中之无迹,难于画境之无迹,这是因为画之象明,书之象晦。书象即意象。意中之象,全在点画,而情态生发于无象之中,所以有迹之为利,无迹之为用。但是书法的点画抒情,以内容寓象,诉于视觉,睹迹而心明。情感因联想而生快,这也是黑白红艺术之妙用。诸家当代都已有深刻研究,但对书风突破的此一领域,我以为还没有完全展开。
总的来说,对于当代书家,不要蔽于黑,举凡行、篇、颖、印,都要看到无迹处之安排。着眼于白的训练,无迹之迹,无迹中之气脉,无迹中开合迎让,打开迫促之空境,彰显书法之天地,有待于当代书家共同探试,以免落后于日人,这是我们一代书法家对书坛新领域的开发,更是时代赋予我们不可辞谢之责任。
(作者为书画家、教授,创立“黾学”学派,创立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全委会荣誉委员)
(《人民周刊》2025年第18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