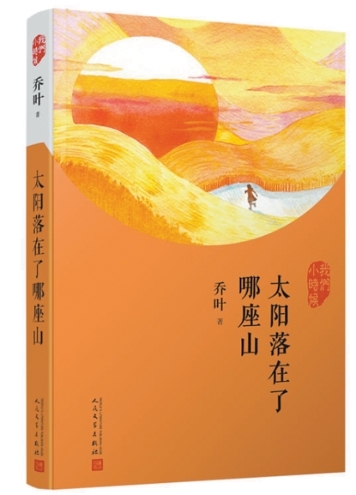
按照以往编选散文集的惯例,我把本书的篇章做了分辑。分着分着就觉得,其实是不大好分的。每一篇都如同一棵小树,树与树之间虽然有行距,俨然独立。但树与树之间,于地面之上枝叶相拂,于地面之下根须相系,着实是难剥难离。
比如“土地上”这一辑里,《土味儿》《蹲苗》等,貌似都是与土地相关,可土地是那么辽阔丰饶,简直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寓言。在“我是一片瓦”这一辑里,瓦,扇子,指甲草,爆米花,等等,虽然也都像是在写物与事,可物与事中怎么会没有人呢?还有“在月光下奔跑”这一辑,固然是在写亲人,而我的亲人们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与乡村密不可分的物与事中。
比如棉田。我刚开始学习小说写作时,就在一个短篇里写到过。前些年我还写过一个童话,写小女孩朵朵在旷野中寻觅自己的智慧之星,夜宿在了棉田里。在准备这部书稿时,我又打捞出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在棉田里睡着了,母亲来棉田里找我,找到后我们母女边聊天边走回家去。这情形如此寻常,但40多年后的今天,我再度想起,方才读懂了母亲彼时过山车般的心境:她呼唤我时的惊慌恐惧,看到我时的愤怒叱骂,回家路上的家常闲谈,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母亲的爱。那时幼小的我,怎么可能懂呢?而多年后,在写下《海一样的棉田里,我像只船》的这一刻,我开始懂了的时候,顿时觉得那天的暮色震耳欲聋。
还有奶奶。我写得最多的亲人就是奶奶。她仿佛是一本怎么读也读不完的书。《我是一片瓦》里有她,《扇子的事》里有她……任我的年少岁月翻了多少个筋斗云,也翻不出来她的手掌心。那么厚实广袤的手掌心,我怀疑自己原本也不想翻出去。
“我们小时候”,这丛书的名字起得好。想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我们小时候”,其间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若有相同,就让经验拥抱。若有不同,或可参差对照——好像用不着这个“若”,相同和不同都一定有。不同之处多在表象,相同之处多在内里。做此判断的依据很简单:都曾经是孩子,都曾有童年。据说花朵们刚发芽时样貌最相近,我们的童年可不就是人生的花朵刚刚发芽时?
说到花,我常会想到《朝花夕拾》这个美妙的书名。每每读到鲁迅先生为《朝花夕拾》写的序,我都觉得很会心:“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我也愿意被这样的记忆哄骗一生。清晨时开的花于黄昏时去拾起,正如那些阔别已久的往事,因为难以忘怀,便在过去多年后,让它们在回望、回顾和回想中徐徐回归, 让它们在字里行间被赋形,被重新检视,被呈现笔端,和现在的自己久别重逢。
当然,此花已不同于彼花。写作让一朵花开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当年,第二次是在当下。在历久弥香的气息中,我一瓣瓣描绘出心中花朵的模样。而于纸上绽放的花比开在枝上的花有着更长久的芬芳,且一旦落到了纸上,花就再也不败。
所以,写作真就是朝花夕拾,真就是这样一件迷人的事啊。
(作者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此文为《太阳落在了哪座山》一书后记,本版有删节。)
《人民日报》(2025年08月22日 第 20 版)
(责编:张若涵)

 010-65363526
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rmzk0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