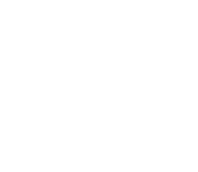艺术上的“风格”和“花样”大不相同。
鉴于目前中国书坛注目于传统技法之研究,而忽于无迹空象之开发,所以作一次发言,重点谈书法是一种融会哲理的艺术。其他艺术虽然也透露出人生、美感、情思等多种观念,而体现在书法之中的却更为集中,充满了辩证的关系。谈“有”的艺术很多,我主要是谈“无”。

有人过于强调形式,那是因为他没进入本质,过于强调形式也会导致内涵的减少,最终导致中国画的衰弱。
老甲似乎也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的职务,甚至也没有接受过什么重要的任务,他在京华,确无“冠盖”。然而在绘画上,尤其是画牛、马一科上,他的画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前人品画都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品画是最直接的批评,是结论记录,可以分等级。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民族文化复兴的推动、对文化艺术健康发展的大力倡导,书法界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但那些夹杂着西方国家有目的地对我们民族文化颠覆的艺术思潮与行为,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明辨是非,增强文化自信,以促进中国美术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按道理,现在画家应该比以前的画家更强,因为学习环境强于前,各种条件也强于前,各地美术馆、博物馆多于前,大型画展常有,电视、录像强于前,消息传播快,看得真切。大画集不但多,印刷也精于前,看精品画集基本上等于看原作,且临摹研究更方便,学校多于前……各类条件都大大优裕于前,按道理,画家水平不应该有更多人强于前吗?事实却相反,什么原因呢?
大家在学习中国书法和绘画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呢?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点上,我们需要深入思考。
笔者在青少年时临摹《兰亭序》9年,几乎一天都没间断,但我在20年前就说过,比较而言,《兰亭序》的书法艺术水平不是最高,注意不是说它水平不高,而是“不太高”,且是比较而言。至少说,《兰亭序》的艺术水平比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要差两个等级。
目前,艺术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莫衷一是、错综复杂,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画得很差也可以通过包装、推荐和宣传来混人耳目。今天我们主要探讨中国画的标准问题,也就是怎样的画才是好的中国画。要知道,任何高深玄虚的理论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画面上。
学书而不是书法创作,我的体会,首先还要形似,即学王似王、学颜似颜,若学王不似王、学颜不似颜,学欧、柳、褚、赵皆不似欧、柳、褚、赵,即形尚不似,而奢言得其神,吾不信也。不仅学欧似颜、学颜似柳不可以,即同是学颜,也必须学《麻姑仙坛》似《麻姑仙坛》,学《颜家庙》似《颜家庙》。我说的“似”主要还是形似。
中国画是什么构成的?笔墨。古人对笔法的讲究比较多,点和线的质量都取于线,短了就是点,长了就是线。中国画在表现过程中,不是特别追求具象如何,而是通过笔墨把心性充分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的要点。
本文不是谈艺术家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而是谈如何对待其他画种的问题。清人见外国画,嘲笑蔑视,“虽工亦匠”“无笔墨”之类的评论太多。所以,中国画在清朝无甚大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外国文化思潮又一次大量传入中国,一部分人吸收学习,一部分人坚决反对。
我所熟悉的不少模仿马蒂斯的朋友,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终于悟到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更可爱。扯几块布条或垃圾堆中的破纸贴在画布上,在自己的身上刺几道伤口,这一类所谓的“艺术”根本无法和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统相比拟。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中国画创作中的中西融合、中西结合问题。对于中西结合、中西融合,我原来既没反对,也没赞成,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才发现还是个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
墨染千年事,笔书万古情。书法里蕴藉着东方的智慧与力量,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愧中华文明之瑰宝。
艺术家(书法家、画家等)能不能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当然有一个标准。这标准不是官位,也不是众弟子和朋友的吹捧,更不是获奖的多寡。这里仅以书法为例,其他艺术可以类推。
书法既然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它必然具有艺术规律上的某些共性。而构成艺术共性的重要特点,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的形象性,一如美术之有形象性,音乐、舞蹈也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形象性一样。这里对书法的形象性作一些探讨。
中国文官治政的朝代,文人在社会上就是一个实际的领导阶层,其他的不可能是真正的领导阶层。所以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即使不做官,只要有知识,大家还会尊重文人。
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应以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凡可振奋民族精神,有益学术研究者,都应博观约取,不受历史定论之局限,为发展新时代的新局面,延续古书优良之传统,作出无愧于前代书家之贡献。
关于国画的当代标准,也是个问题。画家能按照标准去画画吗?凡称画家者,必能创造,必能开拓。所谓“融合”“延续”都不能称为画家,只可称为画画儿人。真正的画家绝不可按标准去创作。但如果画画没有标准,又怎么区分作品的优劣呢?思考很久,结论是国画不可能有具体的标准,但必有形而上的标准,这标准也是在规律之下产生的。
印象派的创始人马奈和莫奈与近代艺术的开山鼻祖毕加索,身居世界美术中心的法国,却都那么醉心于东方绘画之美,这说明世界艺术已生发出一股地下的潜流,其中心正涓涓地向东方移动着。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已经鲜明地露出端倪,绝不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中国画的“唯一性”,除了物质性的基础之外,更有儒、道思想和文官制度的影响,世界上只有中国画有文人画。其他国家的画也有优劣之分,画得好的人称为画家、名画家、大画家或大师,画得不好的不能称为画家,但没有文人画。即使是文人、诗人,画的画也不能称为文人画,诗和文也不能写在画上,而中国画则可以。
“守正创新”在今天是个很响亮的口号,但要问一句,守什么“正”?当然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